华生:须终结卖地财政和融资负债搞发展之路(2)
如果将原分散的乡镇企业用地调整集中进园区,城乡工业用地应当是可以同权的,不过这显然不是很多人所说或心目中所希望的同权。他们希望的同地同权,是乡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城镇商住用地同权同价。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即便同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并不能随便转为商住用地,二者之间并不同权。因此,乡村经营建设用地即原乡镇工业企业用地当然不可能与城镇商住开发用地同权。
另一个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可转用为乡镇企业用地过去只是开了口子,并没有规范和标准,也没有可转用的比例限制。结果当年率先发展乡镇企业的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地区,早已捷足先登,将自己大片的农地转变为乡镇企业用地。典型的如江苏华西村将自己的农田用完了,又通过合并周围各邻村,大大扩展了建设用地,北京郊区的新农村建设典型郑各庄,也是赶着最后一班车把农田都变成了建设用地,从而独具竞争优势。珠三角的相当部分地区更是后来居上,1970年代计划经济时的社队企业发展落后于长三角,然后借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现已将大部分农田变为建设用地,东莞等地的农民现在就是靠把原先的农地全建成厂房出租当房东收租过日子,许多人已经根本不愿也不会再去劳动了。其中,深圳更是一夜之间把全部农地变为农民继续占用的城市建设用地。深圳原住农民这些年来通过多次抢建,已盖起最高达30层的高楼,成了城中村名副其实的地主和房东。
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动作慢、又不敢抢黄灯、闯红灯的农村就完全不同了:别人抢道行车改农田为建设用地,自己还在老老实实种庄稼,等到自己回过味来想占农田搞建设,国家保护耕地的法令已一波波压来。因此,先改农田为经营建设用地的地区已经先发达先富了,遵纪守法听话地区的农民则不让再改土地用途只能种田务农。如果现在不加区分地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农村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商品化货币化,这样地区间的不平等和差距就更大了。显然,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同地同权就会加剧区域差距和社会不公。估计这也是虽然文件中说了同地同权,但实际又迟迟没有起步的重要原因。
其次,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比例最大的一块是农民宅基地。农民宅基地按现行法规定义不是经营性建设用地,而是无偿分给18周岁以上农民建住宅永久自用的福利性用地,有点类似于城市中改革前大量无偿使用的划拨地,它和城市居民的商品房要花钱购买70年使用权的国有住宅用地,权益是不同等的。如果现在将农民宅基地改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上市交易,首当其冲的是要先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但即便如此,农民宅基地无偿获得的永久使用权和城市居民花钱购买来的70年使用权的住房用地,权益仍然是不同等的,因此也不存在简单同权一说。
农民宅基地变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除了要改变现行政策和法律关于宅基地不能对村以外的人流转和转让的规定,同时要规范农民卖了宅基地后,因无处安身再用承包农地建房做宅基地的问题(现在农民废弃原位置不好的宅基地,自行在交通便利的道路两侧的承包农田里新辟宅地盖房的现象并不少见,乡村干部一般也不会吃力不讨好地去费力制止),否则不仅耕地的保护会更麻烦,城乡居民的权利也更不平等了。这样就先要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农村的建筑规划管理,以在宅基地放开交易后避免农民特别是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居民和资本下乡购买农民宅基地在农村乱搭乱建,更要避免建完了不久村子又要撤并,造成更大补偿和浪费。现在这一系列事都还没做或很难实施,是上述思路在农民宅基地这一块还停留在纸面上的原因。
在乡镇企业用地和农民宅基地之外,农村的非农建设用地就只剩道路、桥梁、公用设施等公益用地了。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这一块的用地相对于农村人口倒会急剧增加,还会出现服务于乡村居民点的各种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农村随着人口减少节省下来的建设用地倒是要优先考虑这方面的需要。不过,城市公益用地的性质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没有市场价值,也不能改为经营性使用,农村公益用地和城市公益用地同权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但也并没有什么意义。
除了现存的农村建设用地以外,最有灵活性的一块就是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创造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是一个改革的重大话题,关于这方面的试点和探讨已经很多,兹事体大。
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困境:
成本与风险的恶性循环
综上可见,土地的乱象之所以现在还在越演越烈,主要是改革思路还很不明晰,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卖地财政的不断扩张。由于征收、储备和抵押出卖土地成为各地政府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也只能不断加深。但这一传统城市化模式不仅已经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也孕育着日益增大的风险。
面对巨大利益,农民的土地补偿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上各种保护农民权益的呼声使各种提高补偿的要求更加理直气壮。在《土地管理法》修法酝酿删去30倍产值的补偿上限和按原用途补偿之后,有些专家甚至渲染农民的土地补偿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0倍。但实际上在大中城市的城中村和城郊村的征地拆迁补偿许多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平,补几千万元或几十套住房早已不是新闻。在全国农民家庭资产中位数仅有10多万元的情况下,深圳被称为城中村改造典范的罗湖区渔民村,33户原住民分了6.5万平方米、1300多套住房,平均每家约2000平方米,家家都是几千万乃至上亿资产,更不用说很多尚未改造、自己就已经盖到二三十层高楼坐享地利的原住民以及在我们“补砖头”(即按农民建筑平方米计算价格补偿)的情况下,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以抢建索要高额补偿早已是一个极为普遍现象。
这种情况,造成一方面在工业开发区和远郊区重点工程征地补偿仍然严重不足的同时,整体土地补偿成本不断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负担则在日益加重。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年土地拆迁补偿等支出已占土地出售收入的78%(由于这里只有个“等”字,这个数字被认为是有水分的。但根据国土资源部更早前的披露,不算基础设施投资这个大块,土地拆迁补偿款在前两年已占土地出让金的三分之一左右,近年来还在上升,应是更可靠的数字)。再加上征收、储备土地的资金和利息支出,以及平整土地与基础设施、公益用地等大项支出,地方政府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最后一点非但没有人怀疑,相反正是许多土地财政和政府的激烈批评者也大肆渲染的。这个情况从反面证明了地方政府从土地出售中的收益与其债务相比其实有限,所谓大幅提高农民补偿更不用说提高10倍,就是地方政府把全部土地收益都拿出来也不够的。
- 华生:不触动卖地财政 房产调控使房价越调越高 2013-1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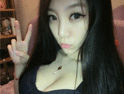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Copyright©2008-2024 沪ICP备10023616号-1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Copyright©2008-2024 沪ICP备10023616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