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陷入上届举债下届还怪圈:经济责任审计边缘化
“耿彦波”式烦恼可能会越来越多。虽然在现有财政纪律下,这位前山西大同市长和他的各级同僚,都要在政府投资中实行集体决策,但在政府性债务背景下,“挖城市长”的舆论效应仍愈发显著。与20年前民众关心基础设施供应带来的便利不同,现在,持有负债意识的居民越来越多。
今年下半年以来,湖南、安徽、厦门等地陆续出台债务管理办法,将政府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纳入党政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湖南省明确提出,对政府过度负债的行为,要追究相关地方政府和当事人的责任。
随着干部流动常态化,一届地方政府任期内有可能经历多位主政者。本报记者采访显示,几乎没有地方能就这些官员的举债行为进行详尽的评估。于是,正常的城镇开发与“换届经济学”交织在一起,主政者的压力更需要用准确的债务信息予以化解。《人民日报》近日甚至刊文指出,欠债越多的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多地出台措施,欲强化对党政领导人的举债约束,被寄予厚望。
横亘在这一改革路上的难题是:两年前,中办和国办出台过类似规定,但是收效甚微;经责债务审计的操作细则并未出台。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尚无地方政府因过度负债而被处罚的先例。
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到,经责债务审计若要“还离任者清白,给接任者明白”,既要调整对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人的考核方式,更重要的是完善经责债务审计的制度设计。
经责债务审计处于边缘
经济责任审计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离任审计,后被引入行政单位,是党管干部的一项措施。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导师李江涛指出,现在对党政领导人的经责审计主要考核经济情况(如GDP),就像当初对厂长经理审计时只注重利润指标一样,忽视了其他指标,比如债务。
2010年,中办和国办联合颁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责审计规定》,首次将“政府债务的举借、管理和使用情况”一项纳入对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经责审计的范围。但这并未改变经责审计中政府债务审计处于边缘甚至被忽视的地位。
“虽然两办颁布了相关规定,但是和操作中对领导干部离任时的债务审计和规定还是有差距的,而且究竟该怎么开展离任时的债务审计,也没有明文规范。”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审计署经责审计课题组负责人蔡春对本报记者表示。
“有的时候,债务情况的变化很少甚至不会写入经济责任报告。”华南某市审计局人士对本报记者坦言,“因为政府机关报表体制是现收现付制,经责审计主要从财政资金审计入手,延伸至资金的去向、使用各方面,举债资金并非财政资金,所以审计也就不会把债务作为重点加以披露。”
此外,由于受人力、时间等审计资源因素的制约,加之中国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异常频繁,经济责任往往很难对一个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内全部时间范围进行一次性的完整审计。
“经责审计虽然范围很广,但是实务审计中审计机关关注更多的是重大经济决策的程序和效果、政府投资工程的实施等情况。债权债务审计现在也会纳入经责审计的内容,但一般不会是审计的重点。”东部某省审计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抽样审计举债大户
近年来,地方债务风险引发空前关注,有学者直斥地方政府只借钱不还钱,坊间亦广泛流传着“上届政府举债,下届政府偿还”的言论。一些见诸媒体的报道曾披露,部分高债务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调动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因而两届政府交接之时的离任审计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些地方开始行动起来。“2011年审计署开展债务专项审计后债务有增无减,又有些违规操作,所以我们将债务审计纳入经责审计。”厦门市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
由于缺乏对党政领导人经责审计的细则,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方式迥异。
“由于人手不足,离任审计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利用债务专项审计的结果,将其写入党政领导的经责审计报告。” 前述负责人说。
前述审计厅人士则介绍,作为经责审计内容的债权债务审计,该省根据重要性原则,着重关注地方举债大户的风险,是一个抽样审计。“不可能将每一笔债务都纳入党政领导经责审计的债务审计之中。”他说。
前述审计厅人士介绍,只要政府领导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举债,审计是认可的。如果债务风险过高,审计人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提醒地方地方政府注意债务规模,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强制性。从目前来看,尚无地方党政领导人因为债务风险过高而承担责任的案例。
“实务审计的时候,即使发现党政领导人任职期间有过度举债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中存在问题,除非存在违规举债,比如夸大抵押资产价值、财政资金违规担保举债。”前述审计厅人士补充道。
长期以来,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经责审计的主要内容一直是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及其效益,这方面的审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地方政府、人大通过的发展规划、财政预决算报告就是其中的一个依据,但是党政领导人的举债合不合适则缺少标准。
蔡春建议,可以将地方政府的举债计划列入政府发展规划纲要或者政府财政预算,并报同级人大通过。这样既可以适当控制债务规模,经责审计时也就有了依据。
“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审计会跟进,会发现党政领导人的举债是不是有计划、有依据,这样的经责审计更有效用。现在的经责审计只能是调查了解党政领导人的举债情况,举债规模合不合适并没有标准来评价。”蔡春说。
相较而言,湖南的债务管理办法更进一步。该省提出要限制市县年度新增债务额度。如是,经责审计时可将其作为合不合适的参照。
审计报告亟待公开
一般认为,其实离任审计原应作为调动官员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先调任,后审计”。因此,离任审计对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责任的评价就大打折扣,对党政领导人的过度举债行为几乎不存在约束作用。
今年2月,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代市长。这次调任甚至引发部分大同市民春节期间上街挽留。据媒体报道,当地一些居民尤其是部分开发商担心后一任领导能否切实履行前一任主政时的征地、拆迁、安置承诺,也不知道政府到底有多少家底,究竟欠了多少债务。
数据显示,“造城市长”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大同市主要城投公司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2008年末的81.82%增长至2012年末的85.34%,同期刚性债务余额由25.93亿增长至96.62亿元。随着组织部门的一纸调令,耿彦波离开大同,上任太原。
“离任审计的时候,领导干部已经离任,过度举债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任中审计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任中举债过多,我们在写审计报告的时候做出风险提示,建议控制一下债务规模。”前述负责人对本报记者称。
前述两办规定指出,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进行任中经责审计,也可以在领导干部不再担任所任职务时进行离任经责审计。
近年来,扩大任中审计是经责审计的一个趋势。山东省审计厅披露,该省在2009年时厅级干部任中审计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任中审计超过一半。
但是官方鲜有公开党政领导负责人的离任审计报告,这也与两办规定的内容不符:审计机关实施经责审计,应当进行审计公示。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最好的方式就是公开经济责任的审计结果,现在审计结果资料相关部门是有的,但是对官员的经责审计还是没有公开。”蔡春说。
- 银监会要求并表监控表外融资 照亮地方输血暗道 2014-01-15
- 部分地区地方债规模过大 明年是否扩赤字存分歧 2013-12-27
- 地方债或将须人大审批 中央不对地方债务兜底 2013-12-17
- 机构称地方债规模超21万亿 1万多家企业法人负担 2013-11-23
- 渣打称预计有1万家独立法人实体负担地方债 2013-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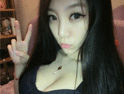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Copyright©2008-2024 沪ICP备10023616号-1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Copyright©2008-2024 沪ICP备10023616号-1